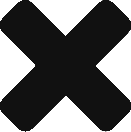那一天,在太浩湖 (Lake Tahoe) 附近的一座山頭上,我們看到了雪。正確地說,應該是冰雹——六月中旬時無聲且迅速的冰雹,重力加上冰凍的雨點,輕打在我們的衣服上。那個時候大概攝氏六、七度,其實沒有很冷,是我們的身體曾經熟悉的溫度。
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們接連搬離了賓州的小鎮,與那裡似乎再也沒有連結。劇烈的生活變動,雙眼所見是不同的風景:溫熱的空氣,炙熱的陽光,風中搖曳的巨大棕梠樹。雖然如此,身體卻還記得許多事情,比如賓州山谷裡的溫度,比如雪。攝氏六、七度,大概就是山谷小鎮裡常有的溫度,你可以感覺得到冰涼的空氣輕貼在皮膚上,它讓你不自覺地拉起外套的拉鍊,卻又想聽腳步踩碎枯葉的聲音,在外面多逗留一會。
那天下午在太浩湖山頭上摸到冰與雪,我們像孩子一樣興奮歡呼,貪婪地吸著每一口沁涼的空氣。我想起初來乍到 State College的時候,研究所的同事開玩笑說這個小鎮就只有三種季節:雪季、足球季,還有無止盡的道路工程作業。那長達半年的冷天,寂靜到只聽得見彼此的聲音的黑夜,曾經都令我畏懼。我對小鎮的情感複雜的,既想要離開,卻也充滿眷戀與感激。
在小鎮裡的研究所的生活有許多痛苦的部分,例如不斷緊縮的體制與資源,面對研究時巨大的無助孤寂,學術場域裡的權力遊戲,那些冠冕堂皇,無視與冷漠,許多的表演⋯⋯。但也因為在這樣嚴苛的環境裡,與朋友們的情誼更加的刻骨銘心。我們各自遠離家鄉到這裡工作、完成學業,我們是在彼此危難的時刻接住對方的人,我們即是彼此的網。想起小鎮時,想起她們的藥品,我們一起遭受過的冷漠——那些傷痕與病。如果研究所的日子多數是在又冷又長的夜裡度過的,那些我們共有過的情感即是長夜裡最溫暖的營火。
來到灣區一個多月了,這裡多是溫煦的風,金燙的艷陽,附近有好幾間我愛逛的韓國超市、亞洲甜品與麵包店。這樣熱鬧多元的城市生活曾是過去幾年的我夢寐以求的,卻在太浩湖山頭上碰到雪的時候想起原來自己其實也挺能夠欣賞肅穆的冬天。孤冷單調的生活其實也有它的況味的。
也是經歷過了這樣的搬遷,我開始不再用所謂「階段」來看待自己的人生。以前習慣用階段或是線性的時間來丈量生活,好像時時記得自己的年歲、哪一年做什麼或是不做什麼,比較能夠有生活的實感。但是這樣的個人年表容易讓人以為階段之間的移動是單向的,我們從上一個階段移動到下一個階段,就此不再回頭,也跟上一個階段沒有什麼關聯。
在大學城更是容易有這樣的錯覺,因為身邊的人群與朋友來來去去,大家都在完成學業後離開,離開了也不再回來。面對職業的選擇也會有這樣的線性時間感,例如離開了學界,就脫離了學者或是教師的身份,好像那些身份是能夠穿脫的服飾,脫下以後就不再與舊的身份有所關聯。
近日不斷頻頻回頭的我,時常覺得無法將自己與自己曾經住過的地方、擁抱過的角色完全切割,它們都曾經在不同的時期豐富了我的生命經驗。即使離開了學術界,仍然覺得自己離曾經研讀過的文本很親近,好像那些作家、評論家的字句都被寫進自己的骨髓裡,我寫過的那些東西也成為了我基因裡的一部份。我仍然喜歡從學者的角度去理解世界。只是,這一次,我不再是在高冷的學術殿堂裡,也不再跟我所觀察的地方、人群分開,而是能夠站在人群之中去觀看。其實,我總覺得自己離開學術界,是為了能夠離寫作、離知識的追求更近。
有時候,離開是為了能夠再訪初衷。看似走的遠了,卻還是頻頻回頭,讓自己跟知識之間的關係保有溫度。
離開了山谷裡的小鎮,離開了習以為常的肅殺秋風和雪,我仍然不斷顧盼流連。在這裡,似乎沒有陽光照不到的角落,疲憊的時候我常常想起鍾孟宏導演的電影《陽光普照》——那種當一切都在活潑地生發綻放,被生活擠壓的個體在豔陽之下找不到可以躲藏的地方,沒有一個讓自己躲在暗處舔拭傷口的角落。走過住家附近的橋下,陰暗之處是尿液與食物餿掉的味道,這裡是無家可歸者躲避陽光的地方,也是他們留下生活痕跡的所在。城市裡的艷陽與陰暗,繁華住宅與簡陋帳蓬,這樣的對比時常讓我不知所措,帶著罪惡感在觀看城市人間生發的一切。
我把關於雪的回憶深埋在心裡,時常想起二月多時一個人散步的公園,一望無際的冰與灰蒙的天空。那裡就是我讓自己安藏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