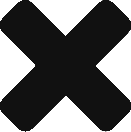一首歌總能在不經意時懾人心神,講出我們心底被壓抑的、不可名狀的渴望。而車上,是我時常聽歌的地方。
小時候坐在爸爸黑色的日產轎車裡,我們一家人通常沒有什麼交流,彼此沉默且壓抑,那個時候耳邊聽的是陳淑樺的〈夢醒時分〉、王傑的〈一場遊戲一場夢〉、齊豫的〈橄欖樹〉,後來還有錦繡二重唱的〈單飛〉與〈學會離開〉。媽媽說過她懷著我的時候總喜歡聽音樂,聽的多是由傳統中國樂器演奏的樂曲,我在她的子宮裡聽多了也培養出對音樂與情緒的敏感度。
妳從小就音樂感受力強,聽完一首歌就會告訴我那是一首快樂的歌,還是傷心的歌呢!」她在車子裡大力讚揚,我在後座透過後照鏡看見爸爸深鎖的眉頭,哥哥看著前方擋風玻璃悶不吭聲。
話語企圖黏著車裡被割據成四方的空氣,而我望向窗外,覺得媽媽言過其詞。不過就是感受歌曲裡的開心或者憂愁,有什麼困難的嗎?
長大以後回想那段經歷,才明白媽媽早已知道我是個對環境與情緒極度敏感的孩子。那個時候「高敏感」這一類的字詞還不普遍,她卻以最直覺,也最直接的方式揭示了我性格中的善感。沒有胎前的記憶,我偶爾幻想自己還是子宮裡沉睡的胚胎,被母體世界外的歌聲喚醒,靈魂大概就是在聽音樂的時候長出來的吧?
青春叛逆期的心高氣傲,父母之間錯綜複雜的恩怨,被包裹在移動的車子裡。媽媽說不要向外張揚我們家發生的事情,然而壓抑造就的卻是各自承受疼痛的經驗,無處訴說,孤寂且無助。黑色的日產轎車把滿溢的情緒裝載,像是裝著困惑的金魚與水的塑膠袋,袋口束緊,金魚無處可去,卻還是可以呼吸。
那一陣子在車裡,爸爸的歌單時常播到李翊君〈這樣的我〉:
「沒有人看過我流淚 以為我從來不懂傷悲
就像在秋天沒有冷的感覺
沒有人聽說我愛誰 以為我寂寞也無所謂
不知道孤獨的時候誰來安慰」
歌詞講的是愛情裡的孤芳自憐與失憶,徬徨少年時的我還沒能全然理解,卻覺得李翊君唱出了我內心那不被理解,渴望得到憐愛的感覺。有限的成長經驗導致我誤解了歌詞,然而誤讀與聯想也萌生了許多可以用以滋潤自己的意義。
這麼說起來,聽歌有時像是在讀文學作品,尤其是那種讓你能夠在困頓的生活中看見一抹霞光的作品。我在或是激昂纏綿、或是悠遠低緩的歌聲中覺得自己被聽見。覺得,我被世界接住了。
***
而多年以後的一個夏日午後,我與先生在車子裡聽著TANK的〈專屬天使〉。車外是北加州的豔陽天,眼前是聖荷西東邊光禿的山腳,綿延的土黃色山丘像極了魔幻沙漠。Tank的聲音像細沙一樣溫柔,唱出了青澀愛情的模樣,那種渴望自己是對方唯一的守護對象的心情:
「沒有誰能取代 你在我心上
擁有一個專屬天使 我哪裏還需要別的願望。」
戀愛,尤其青春期的戀愛,總有種宿命般的絕對感。當時的專情在大人們眼中看來就是鑽牛角尖,而當我也變成三十出頭的「大人」,回首時卻覺得青春期的脆弱與情深,既是侷限,也是因為比大人更懂的珍惜。
「你記得〈專屬天使〉是哪部劇的片尾曲嗎?好耳熟。」我邊滑手機,邊問一旁開車的先生。他笑而不答,知道沒耐心如我會自己尋找答案。
「啊,是《花樣少年少女》!」這才想起來那部我曾經在小學六年級時為之著迷的偶像劇。劇裡,由Ella主演的盧瑞希女扮男裝讀男校,為的是能夠陪伴在吳尊飾演的左以泉身邊。女扮男裝是輕易被識破的套路,然而十二歲的我入戲至深,瑞希與泉的曖昧讓我平凡乏味的上學日子都變甜了。升上國中的夏天,我甚至買了《花樣少年少女》的電視寫真書,皮夾裡放了吳尊的照片。
寫真書與照片騷饒著青春盪漾的心,然而真正烙印在記憶中的是《花樣少年少女》的片尾曲——由S.H.E.主唱的〈怎麼辦〉。車窗外仍是綿延的土黃色山丘,而我迫不及待地與先生分享對我而言別具意義的歌,歌詞呼應偶像劇裡那愛戀對方,卻害怕被發現的心情:
「怎麼辦 感覺甜又酸 偷偷愛你 快樂又孤單
怎麼辦 愛卻不能講 你真討厭 不來幫我的忙」
我喜歡輕鬆活潑的曲調,唱出了暗戀之時的害羞與甜蜜。透過S.H.E.的合聲,大人們眼中的三八被轉化成青春的自信與能量:
「你怎麼可以這樣 笑容打敗太陽 甚至比我還要更好看
我雖然無力抵抗 但是日子還長 總有一天換你 為我瘋狂」
能夠相信世界,相信自己終究會被愛,真好。
***
曾經很癡迷地追劇,跟著戲裡的男女主角揪心,那個窩在二十寸小電視螢幕前守候、渴望感受愛情的時光被〈專屬天使〉喚醒。
一樣在車子裡聽歌,而此刻我已經走過了孤獨徬徨的少年時,是一首又一首歌曲見證了那些不能被訴說的時刻。
車窗外是加州的豔陽天,而車子裡的我聽著歌,在我差點遺忘的旋律與歌詞中與過去的自己相遇,一次又一次。